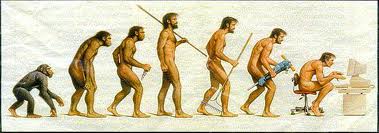纪念查尔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
作者简介:龙漫远,美国芝加哥大学生态与演化学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从事遗传学与演化论研究;陈振夏,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兴趣是基因演化和生物信息学。
一千年前的中原,凡有水井处,皆唱柳词;今天的世界,凡有科学之处,皆说达尔文。
一 超越时空界限与学科藩篱
1809年2月12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生在英国什罗普郡的历史名城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1859年11月24日,他的不朽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而影响历久不衰。从他的家乡到世界各地,不同信仰的人们或欢呼,或沉思,或惊愕,或暴怒,谈论的中心议题就是以自然选择理论为基础的演化学说(Evolu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200年后的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民众都投入了纪念这位科学伟人的盛事: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南非、日本,以及海峡两岸的科学机构和团体,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包括讲演、集会、游行、展览以及出版新书和纪念文集等,来庆祝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与《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位科学伟人及其学说的推崇和敬仰,其热烈程度和波及范围是空前的,超越了国家、地域、政见和族群的界限,成为全人类科学与文化的盛大节日。
达尔文开创的演化生物学,经过150年的发展,不仅广泛渗透到生物学的各个分支,而且深深影响了其他科学领域,甚至在一些意想不到的议题上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应用。知名天体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教授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其畅销世界的科普名著《时间简史》中,借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人类智慧的演化,他认为自然选择赋予人类的推理能力使其得以窥探天体演化的秘密。事实上,霍金对达尔文理论的这种理解是值得怀疑的:自然选择固然青睐能够留下更多后代的个体,但人类的推理能力与其生殖能力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上个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之一,他的学术思想也深受达尔文理论的影响。然而与霍金一样,哈耶克对达尔文理论的理解同样存在着偏差。在远离生物学甚至科学之外,我们还经常可以读到诸如“舞蹈的进化”、“音乐的进化”、“服饰的进化”、“发型的进化”、“文化的进化”或者“建筑的进化”这样的词汇。在与人类自身有关的活动中,东西方都有许多人产生了更多的自信甚至偏见去作价值判断,把演化笼而统之地理解成“进化”——其中的对与错可以留给相关行业中的人士去讨论,但这些词汇的使用已足见达尔文的evolution概念影响之广泛。
在广袤的生物学领域里,越来越多原本不涉足演化生物学的研究者发展出对演化科学和达尔文的兴趣,越来越多原先不发表演化生物学文章的期刊开始设立演化专栏,越来越多的大学建立了与演化生物学相关的院系,人人都试图谈一点达尔文和演化。有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甚至提出,应把是否阅读过《物种起源》作为一个人受过正规教育的标准之一。无怪乎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L. Monod)曾以幽默的口吻说:“演化论的一个奇特好笑的方面,是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懂得演化论!”[Monod,1974]
达尔文似乎正在成为科学领域的“圣人”。
二 演化是什么?
“演化”一词译自英文单词evolution,广义指一切随时间发生变化的现象,在生物学中则特指生物个体及种群随时间演变的过程或事件。然而,翻译成中文后的evolution一词却被有的教科书甚至辞典(例如《辞海》、《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错误地定义为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进化发展过程。事实上,作为生物学的一般过程,“演化”并不含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绝非一个必然进化的过程。达尔文把evolution严格地定义为“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可译为“饰变演替”或意译为“渐变演替”)[Darwin, 1859]。而100年前严复也首先将其准确地翻译为“天演”,意指发生在自然界(“天”)的生命变化(“演”)。其中的含义是生物没有长远的方向性,它既可以由简单到复杂地进化,也可以由复杂到简单地退化。
虽然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人意识到演化的存在,但正是他首先以精细的观察和严密的推理证明了演化事实的存在。1831年12月27日,年轻的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搭乘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帆船(HMS Beagle)开始了长达5年的海上生活 [Darwin, 1839]。1835年9月至10月,船行驶至南美洲厄瓜多尔附近的加拉帕哥斯群岛(Galápagos),达尔文在这里发现不同岛屿上分布着不同种的巨龟,还见到了在其它地方所没有的13个新的物种即“达尔文地雀”(Darwin’s finches)——这些鸟的喙的形状大小呈现出一个渐进连续的分布趋势,应该同其食物来源紧密相关。达尔文推测,美洲大陆的一个物种最初迁移到这个原本缺少鸟类的群岛,然后适应各个岛屿的生存环境(特别是食物种类)而逐渐演替成这些不一样的物种[Darwin, 1839]。此外,达尔文在演化概念上的贡献还包括:(1)“共同祖先”(common ancestor),即不同物种是由共同的祖先演化而来的,所有生物组成了一株巨大的生命之树;(2)“渐进变异”(gradualism),即物种间或大或小的差异都是演化过程中微小差异不断累积的结果;(3)“群体内的变异”(populational change),即演化是靠物种群体内拥有遗传差异的个体的频率改变所实现的。
达尔文最重要的贡献是揭示了演化机制,即自然选择机制的存在。他把自然选择定义为:
如果对生物生存有利的变异一旦出现, 具此变异特性的个体就一定会获得最好的机会在生存斗争中保存自己;这些个体在强大的遗传原理作用下就倾向于产生具有类似特性的下一代。为简便起见,我把这一[有利变异的]保存原理称为自然选择。(If variations useful to any organic being do occur, assuredly individuals thus characterized will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being preserved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and from the strong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they will tend to produce offspring similarly characterised. This principle of preservation, I have called,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Natural Selection.)[Darwin 1859, p. 498]
这一定义包括了两个重要条件:(1) 生物群体的个体中存在影响生存与生殖能力的变异;(2) 这些变异是可遗传的。这两个条件下导致的自然选择结果,是能留下更多后代的变异体替代了那些不利于繁衍后代的变异体,使得物种更适应环境。因此,演化又可以定义为变异体或基因频率的改变。
达尔文通过对以其名字命名的地雀的细致观察,为自然选择过程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明。演化学家们已经从动植物系统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中积累了大量证据,揭示了演化事实,并且描述了演化过程的特征和模式。现在,“演化”一词有了更加完备的内涵。人们已经认识到,个体间的生存竞争并非必不可少,只要存在生存与生殖能力的微小遗传差异即可改变一个群体的构成或促使演化发生。这种情形已经得到证明,例如分布在戈壁沙漠的稀少物种,哪怕其个体间不存在生存竞争,但只要彼此间存在生殖能力的遗传差异,就会发生演化。
尽管达尔文把自己的科学理论同宗教信仰看成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领域[Darwin, 1876],但他的理论推翻了西方社会上流行的“神创论”,否定了上帝七天内创造世上万物和人类的神话。而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多奉基督教教义为认识世界的最高准则,因此挑战《圣经》年代学的达尔文经受了严峻的社会挑战。一些信奉上帝的自然科学家对生物学领域的这场革命也抱着敌视的态度,攻击达尔文和他的学说;而极力维护基督教权威的教士们则斥责达尔文的演化论是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尽管社会上出现了以教会为主导的对演化论的全力围攻,但那些立足于盲目信仰的攻击无法抹杀达尔文通过事实与科学方法所阐述的结论。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英国国教英格兰圣公会还发表了一个声明,为当年在否决达尔文理论上的“过当自我防卫”与“过于感情用事”向达尔文,也向今天的公众正式道歉。[Wynne-Jones 2008]
达尔文为整个人类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并因此成为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指出在纷繁芜杂的生命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一般规律。他的演化机制为包罗万象的生命科学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基础,生命科学的大厦将分崩离析。
三 达尔文的缺陷
达尔文是一位科学巨人,但他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圣人,也不是全能的先知。这一点凸显在他为其自然选择理论的第二点——变异的遗传基础所做的努力上。首先,他正确地意识到,如果没有遗传基础,那么对变异的选择在演化中就是无效的,于是他竭力构建遗传理论。一开始,他相信当时流行的“融合遗传”假说。按照这一理论,父母亲的遗传物质在子代会发生融合,子代的变异只是亲代混合的结果。这就像红墨水和蓝墨水倒在一起,混合液是另一种颜色,分不清是红是蓝。“融合遗传”假说的后果是,个体变异经过若干世代的融合将被不断地稀释并最终丧失,而无法得到积累。所以,这一假说无法解释新的遗传变异如何在物种中演化。
达尔文意识到这一理论的缺陷,所以后来改变了观点。他在后半生中用了大部分精力来构建新的遗传理论——“泛生论”(pangenesis)。他认为生物体各部分的细胞都带有某种特定的称之为“微芽”的遗传成分,这些成分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性质上发生改变,并可以集中于生殖细胞和遗传给子代。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获得性状遗传观点。虽然达尔文曾把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的演化论贬斥为“垃圾”,但他也不得不从这种“垃圾”中寻求出路。然而,他倡导的泛生论缺乏实验证据,其主要部分仍然是错误的,达尔文显然对这一理论也不满意。在去世前不久,他干脆放弃了建立遗传理论的努力。
事实上,当达尔文正在为遗传机制苦恼之时,位于奥匈帝国一所修道院中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生物学家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已经通过豌豆杂交实验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位后来被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修士选择观察简单的质量性状,如花的颜色、豆荚的形状、豆粒的形态等,追踪那些双亲存在差异的性状在后代的表现,从而揭示出遗传学的两个基本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检验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让他看到了遗传的秘密:生物体存在着分别来自父母的两套遗传信息,每一遗传信息都是由粒子样的间断的遗传因子所构成。据说,孟德尔曾寄给达尔文一篇论文,报告他对遗传机制的发现。可惜的是达尔文一直到去世都没有打开过这封信。
如果达尔文打开了孟德尔的信,演化科学或者达尔文理论的发展就会是另一种面貌吗?达尔文在他的后半生就不会在错误的理论上浪费时间吗?不一定。第一种可能是,他能理解孟德尔的工作(从实验到理论分析),但他不认同,因为孟德尔并没有指出变异产生之源。第二种可能是,他并不理解孟德尔的理论分析,完全无法判断其结论的真伪。因为孟德尔使用了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而这些数学能力是达尔文所不具备,至少是忽视的。这里所说的第二种可能不是没有根据的:达尔文留下的资料表明他做过类似孟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但他的分析没能达到孟德尔的水平。显然,达尔文虽然善于观察和综合,但是并不擅长更加抽象的数理推导。
四 建立演化理论的遗传基础
孟德尔对遗传机制的发现超前了整个时代35年,而他得到演化领域的普遍承认则是近70年以后的事。直到1900年,荷兰植物学家狄弗里斯(Hugo de Vries)和德国植物学家科林斯(Carl E. Correns)才同时独立地“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定律。但是,演化学家们仍不能正确评价孟德尔发现的巨大意义,因为达尔文理论认为,只有连续变异的数量性状(如身高、体重)才对演化有意义,而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大都控制具有较大效应的质量性状。
1911年以后,摩尔根和他的学生们革命性地发展了基因的概念。他们应用孟德尔因子与性染色体的对应关系,把原本抽象的概念定位到了染色体上。从此,基因有了物质基础。这些遗传学概念的进步,为此后演化研究的“现代综合学派”(Modern Synthesis)的革命打下了基础。这场发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科学运动,解决了让达尔文遗憾终生的问题——演化发生的遗传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演化是无法理解的;而没有这一遗传学的综合,关于演化的进一步研究也没法深入下去。今天,其它学科的一些研究者们也在思考演化科学史上这一革命的实质,试图在相关的研究领域进行新的现代综合。这一类的努力向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现代科学中有哪些基础性的、概念性的成就非得综合不可?毕竟,纯粹形式上的模仿有可能东施效颦,并不能发展出有意义的科学研究。
演化研究中的现代综合始于三个划时代的人物:英国的费歇尔(R. A. Fisher)、霍尔丹(J. B. S. Haldane)和美国的赖特(Sewall Wright),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著作构建了演化的遗传学基础。其中,费歇尔的遗传演化模型最接近达尔文的原意,即演化发生在一个大的群体中,控制微小适合度变异的新遗传基因在自然选择下有效地被固定 [Fisher 1930]。他进而发展出自然选择的遗传定律(the Theorem of Natural Selection):一个物种的适合度总是被自然选择所增加,其世代间的增量正比于这一物种的适合度所具有的遗传变异量。费歇尔的演化理论是决定性的,具有强因果关系。霍尔登总结了种间和种内遗传变异的资料,并且指出了二者的联系。他提出了遗传载荷理论,指出由于群体大小的维系,一个物种内发生的自然选择不可能是任意大的[Haldane 1932]。赖特则在建立基因频率改变的群体遗传理论体系的同时,开创了一个当代演化研究最重要的概念:演化发生的随机性[Wright 1931]。他发展的数学模型表明,物种群体大小的有限性赋予了生物演化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的程度由各种演化因子(如群体大小、选择强度)决定的概率分布来度量。于是,有意义的问题不再是一个演化事件是否发生,而是这一事件以多大的概率发生。这一不确定性概念的提出,为后来的一场分子演化的革命,即中性理论的诞生奠定了概念基础。在赖特的世界里,一个曾经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演化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这些理论都把演化定义为物种群体内基因频率在世代之间的改变。这一定义实际上反映了演化发生的真实图景:一个新的遗传变异体在物种内某个个体身上形成了,它在群体中的频率会因为各种演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最后到达两种边界状况之一——或者从种群内完全消失,或者得到固定并成为物种的一个特征。这一明确定义使得理解和分析演化的全过程成为可能。事实上,上述三人的成就从本质上便得益于这一定义的完备、清晰和精确化。
怎样把当代综合理论和实验观察联系起来?
俄国出生的美国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T. Dobzhansky)是实验演化遗传的主要人物。作为摩尔根的助手,他把实验室的果蝇研究延伸到了实验室之外的自然界,试图直接观察自然物种群体中的变异,并找到生存环境同果蝇遗传变异之间的联系。他最早观察到果蝇自然群体存在染色体变异,但并没有发现这些变异同果蝇所处的生存环境有任何关系。由此,他认为这些变异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协同适应复合物(coadaptation complex),而成为生物多样性的来源之一。这一理论并没有成功。他的著作《遗传学与物种起源》(“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1937)概括了生物学现代综合学派的主要成就,从而为其赢得盛名。而他晚年留下的名言:“若无演化之光,生物学中就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则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演化学家和许许多多其他学科的生物学家。
在植物演化方面,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的斯特宾斯(George Ledyard Stebbins)将达尔文理论同植物遗传结合起来研究植物物种形成过程。他的名著《植物的变异和演化》(Variation and Evolution in Plants,1950)从种内种间的形态生态变异、生殖隔离过程、植物较普遍的多倍化过程及化石证据等方面阐述了植物物种形成机制和演化速度,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植物演化及系统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比较了化石记录中物种演化的速度和模式,研究了大陆漂移与哺乳动物分布和灭绝的关系。在其名著《演化的速度和模式》(Tempo and Mode in Evolution,1944)中,他把古生物学的成果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遗传基础相结合,发现达尔文定义的群体水平上的演化–个体变异频率的改变,或称之为微演化(microevolution),足以解释古生物学化石资料显现的宏观演化(macroevolution)模式。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迈尔(Ernst Walter Mayr)则以鸟类为观察对象,研究物种的概念和物种形成的一般理论。他在名著《系统学与物种起源》(Systema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1942)中提出了一个广为应用的以考虑生殖及环境和生活史等因素为特征的物种概念:生物学种的概念(biological species concept)。
五 来自分子变异的挑战
1966年在演化生物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不寻常的一年。在此之前,虽然偶尔会观察到染色体和个别基因的变异,但是人们相信一个物种的个体之间在分子遗传水平上是很相像的,因为这些个体都是在一场自然选择中保留下的优秀个体的后裔。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芝加哥大学教授陆文顿(Richard C. Lewontin)的实验震惊了当时的人们。他与同事胡比(Jack L. Hubby)合作,改进了同工酶电泳(isozyme electrophoresis)实验并将其引入果蝇演化遗传分析,从中第一次惊讶地发现,果蝇物种个体间存在蛋白质分子层面的较大差异:在他们所分析的21个酶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中,有9个(43%)存在差异[Lewontin & Hubby 1966]。他们推测,如果这些差异会带来功能上的差别,那么就会导致自然选择让一部分个体由于其功能不利于生殖而被淘汰;但是根据霍尔登遗传载荷理论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有利功能的果蝇个体甚至很难产生足够多的后代以维持其种群的大小。因此,他们认为已有的自然选择理论难以解释观察到的巨大变异。在此以后,人们用同样的技术又分析了上千个物种,确证了陆文顿-胡比观察结果的普适性。
1983年,哈佛大学年轻的研究生马蒂·克里特曼(Marty Kreitman)更是把对群体内个体间分子变异的观察首次延伸到编码基因的DNA序列,发现了今天广泛应用于生物学研究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结果检测到更高水平的个体间变异 [Kreitman 1983]。他检测到了基因分子的不同部分由功能不一所造成的选择上的差异,只是这样的自然选择并不是达尔文理论预期的引起适应性变异的正选择,而是同中性演化理论不相矛盾的负选择(purifying selection)。
这些大规模分子变异的观测结果为演化科学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果自然选择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客观存在的变异,那么还有什么其它的演化机制能够控制生物的可遗传变异这一演化之源呢?达尔文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在基因的分子水平上第一次遭到来自科学自身的严重挑战:已有的理论不能解释观察到的现象。
六 孰是孰非
陆文顿-胡比实验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的演化生物学制造了危机。这是达尔文理论在分子水平上的危机。对于富有创造精神并乐于接受挑战的科学家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比应对科学危机更刺激有趣的了,因为按照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正是危机带来了探索重要问题和进入全新领域的最好机遇[Kuhn 1970]。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不能说是没有创造力、但对现有理论深信不疑的科学家而言,放弃原有理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两类科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延续近30年的论争。有趣的是,论争双方在感情上都很投入,甚至不能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但论争的结果却并不是简单的谁是谁非,而是一场革命性的探索,从而使人类在分子水平上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关于演化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在研究手段上有了巨大的飞跃。
在分子群体遗传学兴起的同时,由于基因测序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迅速进步,基因分子的序列和功能资料得以剧增。通过这些研究,人们渐渐开始怀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分子水平上的普适性。1968年,日本群体遗传学家木村资生(Motoo Kimura)根据对蛋白质序列的研究结果首先提出质疑。他直接挑战了认为自然选择是主要演化力量的主流观点,首次提出中性突变的遗传漂移(genetic drift)是分子演化的主要原因[Kimura 1968]。美国分子生物学家金(J. L. King)和朱克斯(T. H. Jukes)也在1969年得到了与木村相同的结论。[King & Jukes 1969]
木村资生系统地发展出一整套中性演化的数学和生物学理论,发表了划时代的专著《分子演化的中性理论》(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Kimura 1983]。按照这一理论体系,分子水平上绝大部分的变异都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对生物个体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并不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这些变异通过随机漂移在群体内发生频率的改变,最后消失或在种群中固定下来。同许多仅靠文字描述的生物学特别是演化生物学的理论相比,中性演化理论为种内和种间的变异提出了可证伪的数学预期,因此有可能直接对中性理论的假说进行验证。其中一个重要的预期是:中性突变的发生率等于演化的速率。这样就把种内变异与种间差异在数量上联系起来了。
从表面看,中性演化的发现是对达尔文演化理论的反驳,一个演化理论的初学者很容易落入谁是谁非的简单二元判断。但是,分子演化学的研究在中性理论诞生以后30多年的发展却超越了这一简单思维方式。一方面,中性演化是对达尔文理论在分子水平上的补充(还有科学家把中性变异的概念延伸到高层次生态水平上),提出了并非一切演化都是适应性演化的结果,在其中机遇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中性演化的数学预期,常常被分子演化学家们作为重要参照标尺来检测达尔文式的正向选择。其中广为应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中性检验”。它基于中性条件下三个方面的原理:(1)种内变异的中性期望;(2)种间演化的中性期望;(3)种内变异与种间进化速率相关。这一研究路线以中性假说作为零假设,结合统计检验方法分析实际观察资料,从而检验正向自然选择的可能。它所带来的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分子水平上对适应性演化的探索,鉴别出大量正向自然选择的分子变异,并使得对基因起源的研究成为可能。运用这些方法,我们探测出新的基因也在达尔文适应性过程中起源和演化,发现基因起源是物种演化的重要遗传机制演变过程[Long et al 2003; Kaessmann et al 2009]。这就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判断框架,导致了对基因和基因组分子水平上伴随着遗传漂变的适应性演化的发现。这是理性的凯歌,是科学的进步,更是达尔文的胜利。演化科学的发展就是如此的奇妙。
七 达尔文理论与中国
达尔文对演化事实和演化机制的发现,导致了西方对人与自然认识上的空前变革,为生物学提供了统一的概念基础。他的思想同样对中国的社会与科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我们把“社会”写在了“科学”之前,是希望反映达尔文对中国影响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虽然两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同时这暗示了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境遇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与中国的近代史直接相连。这是一个较大的课题,不可能在这样一篇论述整个演化科学发展历史的文章中详细论及。但是通过一个极简要的介绍,已足以显示达尔文对中国社会和科学的巨大影响。
1. 社会影响
中国,一个曾经以“天朝”自居、目空一切的古老帝国,在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外强侵略和凌辱之后,不得不痛苦地面对现实,承受任人宰割的命运。从《南京条约》到《北京条约》,从香港到台湾,满清政府一边赔款一边割地,庞大的帝国在风雨中飘摇,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不堪重负。一些有识之士不甘神州沉沦,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他们把西方富强的原因归结为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在全国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
然而,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自强运动的破产。这次惨败直接刺激了一个人,一个曾去英国学习“坚船利炮”之术,而回国后不再走技术救国道路的人——严复。他在英国显然看到,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上还有着更重要的思想理念、经济制度、科学系统等超越简单技术层面的力量。他开始在书房里奋笔疾书,翻译西洋学术名著,希望借此开启民智,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而以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演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为底本的《天演论》正是他翻译的第一本书。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自称“达尔文的斗犬”。《演化论与伦理学》是一本宣传达尔文学说的通俗小册子,严复有意选译了其中论述演化的部分,并结合达尔文演化论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又借用中国典籍中的若干观念和词语,可以说是半翻译半评述地完成了一本符合在中国传播需要的书。严复希望通过这本书回答困扰着中国人的两个重要问题:中国为什么一再挨打?中国是不是就要亡种亡国?
严复告诉中国人,演化是普遍规律,不仅适于自然界,也适于人类。他试图告诉中国人,虽然国运岌岌可危,我们仍然能够“与天争胜”,在自强奋斗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严复十分欣赏赫胥黎以“与天争胜”的观点来匡正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的“末流”之失。《天演论》在向中国人敲响振聋发聩警钟的同时,支持了方兴未艾的变法自强运动。这样的思想迎合了中国当时特殊的政治与社会需要,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在《天演论》出版后,不论是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孙中山、邹容,都读过或提到过这本书,并把达尔文学说运用于自己的政治理论中。就这样,原本是一种科学理论的演化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化身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口号[Pusey 1983]。它给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广,以至于直到今天,严复所创用的“物竞”、“天择”等术语仍然家喻户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接受达尔文演化概念最普遍的国家之一,尽管许多人一直“误读”达尔文的演化理论为“进化”理论。[张伟、刘旸 2009]
2. 科学影响
达尔文的演化论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思潮,特别是中国人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看法,也同样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发展。首先,从五四时期开始,演化论已经越来越被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而非政治思想来传播。20世纪初,留德工学博士马君武首先将《物种起源》引入中国。1902年到1903年间,马君武先后将《物种起源》中最重要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择译为中文,并以《达尔文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单行出版。1920年,马君武译《达尔文物种原始》由中华书局出版,16年间再版了12次。除了马君武之外,周建人、叶笃庄和方宗熙,以及谢蕴贞、伍献文和陈世骧等人也分别翻译了《物种起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宣扬达尔文演化论的译著和文章开始在中国传播。
中国近代的生物学研究是在达尔文演化思想的框架下产生和发展的。上个世纪初,以秉志为首的一群中国留学生聚集在康乃尔大学的所在地旖色佳(Ithaca),决定成立中国科学社,在国内发展科学事业。结果之一是20年代末在北平成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专门从事生物学的研究,秉志和胡先骕分别带领了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这些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创始人在30年代进行了第一个壮举。他们在全国范围系统地采集动植物样本,收集到15万份植物标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编纂委员会 2008]和近12万份动物标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史编撰委员会 2008],并对之进行分类,为中国的动植物物种分布作了奠基性的工作,从而开始了中国科学家关于演化系统和演化过程特征的研究。例如,1940年,秦仁昌以5条演化路线描述了蕨类植物32个科的起源关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编纂委员会 2008]。另一方面,杨钟健于20世纪初领导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开创了中国古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后来这一机构发展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和裴文中等人领导的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就已经是在达尔文演化理论框架下对人类演化所开展的明确研究。这些接受了达尔文理论的中国生物学先驱者们为现代中国生物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广阔和牢固的基础。[李传夔 2009]
八 结语
通过以上评述的有关历史和纪念活动,我们看到,达尔文及其巨著问世以来,对科学事业和人类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他从根本上对生命在时间过程中的演替,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演变过程的理性探索奠定了概念和事实基础。他的演化理论是生命科学纷繁研究领域统一的基础,为生物学家们理解生命现象提供了一类最有价值的思想方法。但是,达尔文本人不是无所不知的圣人,他在演化的遗传基础方面的缺陷由孟德尔的工作填补,并为后继的大综合演化学派、中性演化学派以及演化发育研究提供了基础,使演化生物学发展为一个前途广阔的研究领域。他的思想对中国社会在20世纪初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从一开始就为包括动植物学和古生物学在内的生物科学在中国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概念框架。一句话,达尔文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
致谢 作者真诚感谢以下学者卓有见地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洪德元和葛颂,美国密西根大学仇寅龙,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所张德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顾红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弥曼和周忠和。我们也非常感谢葛颂、张德兴、周忠和、仇寅龙慷慨赠送生物学史籍和文献,它们对我们了解中国当代演化科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李传夔 2009.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简史》(待出版).
张伟、刘旸 2009. 进化论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背后. 《中国青年报》. 2月25日.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史编撰委员会 2008.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 北京: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编纂委员会 2008.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Darwin, C. R. 1839.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In: The Darwin Compendium. 3-410. (2005 by Barnes & Noble Publishing, Inc.)
Darwin, C. R. 1859. The Origin of Species. In: The Darwin Compendium. 413-726. (2005 by Barnes & Noble Publishing, Inc.)
Darwin, C. R. 1876.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In: The Darwin Compendium. 1579-1874. (2005 by Barnes & Noble Publishing, Inc.)
Dobzhansky, T. 1937. 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isher, R. A. 1930. The Genetical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dane, J. B. S. 1932. The Causes of Evolu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Kaessmann, H., Vinckenbosch, N. and Long, M. 2009. RNA-based Gene Duplication: Mechanistic and Evolutionary Insight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0: 19-31.
Kimura, M. 1968. Evolutionary Rate at the Molecular Level. Nature 217: 624–626.
Kimura, M. 1983. The 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ng, J. L. & Jukes, T. H. 1969. Non-Darwinian Evolution. Science 164: 788–798.
Kreitman, M. 1983.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at the Alcohol Dehydrogenase Locus of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Nature 304: 412–417.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wontin, R. C. & Hubby, J. L. 1966. A Molecular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Genic Heterozygosity in Natural Populations. II. Amount of Variation and Degree of Heterozygosity in Natural Populations of Drosophila Pseudoobscura. Genetics 54: 595-609.
Long, M., Betran, E., Thornton, K., and Wang, W. 2003. The Origin of New Genes: Glimpses from the Young and Old. Nature Reviews Geneticst 4: 865-875.
Mayr, E. W. 1942. Systema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nod, J. L. 1974. On the Molecular Theory of Evolution. R. Harre ed. Problems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1-24.
Pusey, J. R. 1983.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son, G.G. 1944. Tempo and Mode in 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tebbins, G. L., 1950. Variation and Evolution in Plan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S. 1931. Evolution in Mendelian Populations. Genetics 16: 97-159.
Wynne-Jones, J. 2008. Charles Darwin to Receive Apology from the Church of England for Rejecting Evolution. Telegragh. September 16.